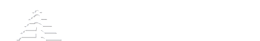Title | 第二节 神韵论的历史流程 |
|---|---|
Creator | |
Subject | |
Description | 第二节神韵论的历史流程 作为古典主义的诗学理论,神韵说实际上继承了古代诗学中卉衍讲,,Z宗0.ii砷L 传统,明代七子派属于那个传统,第一、第二期古典主义诗学本质上都属于那个传统,尽管其中也有很多差别。除了儒学为核心的正统诗学之外,古典诗学还有另外的传统,神韵说继承的也是一个源远流长,而且在诗界影响很大的传统,这个传统作为正统诗学的补充而存在,实际上更多地集中了中国古代诗歌艺术论的精华,值得我们进行整理和总结。 此传统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南朝。南朝是中国历史上文学批评产生飞跃的阶段,其中最突出的是诗歌理论。中国第一部诗学专著——钟嵘的《诗品》即出现在那个时期。可以说它就是神韵说最早的源头。王士稹说过,“余于古人论诗,最喜钟嵘《诗品》、严羽《诗话》、徐祯卿《谈艺录》”,“钟嵘《诗品》,余少时深喜之”(《渔洋诗话》)。钟嵘《诗品》对神韵说的影响体现在哪里呢?最重要的是“滋味说”。钟嵘在《诗品》总论中说: 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岂不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耶!故诗有三义焉,一日兴,二日比,三日赋。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以味言诗,乃钟嵘诗学的一大特色。其实稍早于钟嵘的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已经使用这个词,《明诗》篇云“至于张衡怨篇,清典可味”,《隐秀篇》又有“深文隐蔚,余味曲包”,等等。但是《文心雕龙》体火思精,包罗万象,诗味说不是它的理论主干。而钟嵘的《诗品》—————i..—....................。....~.——。.—::.......——,—,,,...................,—..........——..............一———.—.。———.........。—..——,................—,。.,—..........J———————..一——则是以滋味说为其鉴赏论主干之一的。钟氏滋味说有这样几个重要的特点:一,抒情。“指事造形,穷情写物”,落实在“穷情”上。“闻之者动心”,能动人心者惟有情,犹如食之人嘴,能美人口者惟有味一样。所以“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享受食品时,自然不需要研究营养成分。滋味是生理性的,与人之本性相连,情感是直觉性的,由心理而生理,也与人之体性相连,以味言诗,其妙在此。二是余味说。“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以余味释“兴”,始于钟嵘。钟嵘之前,兴只是一种与比相类的表现手法,到钟嵘这里,兴成为抒情诗的一大基本特点,即意在诗外。钟嵘抓住了中国诗歌一个普遍的特点,并要求将这种特点予以强化和突出,“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这是对中国抒情诗的进一步定位,对于后代诗歌创作的影响是深远的。 至于诗歌缘情的源泉,钟氏也有论述: 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晨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这段话中罗列了两类触发诗情的背景,一类属于自然界,另一类属于人类社会。“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由身边的遭遇而发兴作诗,本是应有之义,而当时膏腴子弟,轻薄之徒,“终朝点缀,分夜呻吟”,附庸风雅,无痛而吟,故钟嵘予以强调。而列自然现象与人际;遭遇同畴,则颇具慧眼。钟氏总论开头还有“气之动物,物之感人,—!i一了———一…一—————————————————”~…一…~卉俘讲广Z采志”俄L 该如此。其实刘勰《文心雕龙》在《物色》篇中对这方面也有精彩论述,尤其关于物我交流的部分,其赞辞日:“山沓水匝,树杂云合。目既往还,心亦吐纳。春日迟迟,秋风飒飒。情往似赠,兴来如答。”南朝宋齐时期,正是山水诗初兴之际,两位批评家的论断,体现了这种创作的趋势。以上这些是“滋味说”产生的土壤之一。 除“滋味说”以外,另一对“神韵说”发生影响的是“直寻说”。如果说滋味偏重于从欣赏谈诗,直寻就偏重于从创作谈诗: 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干用事?“思君如流水”,即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惟所见,“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讵出经史。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作者主张吟咏情性,主张以滋味品诗,所以必然反对堆砌学问,反对探讨义理。原因很简单——“淡乎寡味”。直寻是将心中涌起的感受原汁原昧地吐露出来,不经过加工、修饰,不做第二番手脚,作者又称此为“自然英旨”。钟嵘提倡的是直觉体验,一种灵感式的触发,反对的是意识的介入,理智的参与。关于这一点,晋代的陆机在《文赋》中也有所论述:“若夫应感之会,通塞之纪,来不可遏,去不可止。藏若景灭,行犹响起……是以或竭情而多悔,或率意而寡尤。虽兹物之在我,非余力之所劾。故时抚空怀而身惋,吾未识开塞之所由也。”在性质上讲,直寻跟“感会”包括刘勰的“神思”属于同一类东西。只是钟氏将直寻跟用事、说理对立起来谈,更加突出了这种创作思维的特殊性。后来王士稹即引用钟氏直寻之说反对拟占主义,反对当时学问为诗的风气。可见直寻跟神韵也是有关 创作的黄唐代人的论较其他以殷瑶的有一段序 夫文有神来,气来,情来。有雅体、野体、鄙体、俗体。编纪者能审鉴诸体,委详所来,方可定其优劣,论其取舍。至如曹刘诗多直语,少切对,或五字并侧,或十字俱平,而逸驾终存。然挈瓶庸受之流,责古人不辨宫商徵羽,词句质素,耻相师范。于是攻异端,妄穿凿,理则不足,言常有余。都无兴象,但贵轻艳,虽满箧笥,将何用之。自萧氏以还,尤增矫饰。武德初,微波尚在,贞观末标格渐高,景云中,颇通远调,开元十五年后,声律、风骨始备矣。此段文章中作者回顾了齐梁以来诗歌创作的状况,批判了南朝绮靡鄙俗之风,张扬了建安时代刚健爽朗的风格,对开元以来的盛唐之风作了充分肯定。最后,提出著名的声律、风骨相结合的论断。有人据此认为,唐代诗歌的主流就是声律与风骨的结合,但是忽略了一个重要因素。该因素殷瑶已经指出来了,他称之为“兴象”。全段话中,开首有“夫文有神来、气来、情来”,中有“都无兴象,但贵轻艳”,后有“景云中,颇通远调”,三句话,核心在于“兴象”这一概念。兴象是指自然景物对诗人造成了感动后,在作品中转化成的浸透作家情感的山水万象。此概念是殷瑶对唐诗当中大量山水意象的~ 诗k理忆瑶一黼眠蝴协栅一他与啪瞒醮~一~一一~ ~ 一一一一一限一睇郁酬勤鹣科一⑦j运娄÷l去 动予以关注。如集中他评常建“其旨远,其兴僻,佳句辄来,惟论意表”;评刘慎虚“情幽兴远,思苦语奇”;评陶翰“既多兴象,复备风骨”;评孟浩然“无论兴象,兼复故实”;评储光羲“格高调逸,趣远情深,削尽常青”;等等。由此可见,兴象的重要性在殷瑶那里实际上并不亚于声律与风骨。今人甚至有认为兴象为唐诗之特性的:“如果说,风骨、兴寄、声律之类,在唐人还属于前者师承,那么兴象就是唐诗特有的美学境界。”(陈伯海《唐诗学引论》正本篇)兴象这一概念确为唐人所自创,其所包含的内容却是六朝以来创作中就已存在的。从理论上说,兴象是神韵的前驱之一。王士稹本人确曾将兴象与神韵并提: 唐末五代诗人之作,卑下嵬琐,不复自振,非惟无开元、元和作者豪放之格,至神韵兴象之妙,以视隋之季,盖百不及焉。(《带经堂诗话》卷五)联系王士稹早年选唐人律绝句为《神韵集》,可以推断作者把神韵和兴象并视为唐诗的重要特质,它对于神韵说的启发是明显的。 中唐皎然的批评专著《诗式》在唐代神韵系统的诗论中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皎然论诗以谢灵运为宗,实际上他的理论超出了谢诗,属于唐代创作规律的总结。其中尤可重视者是关于文外重旨的论述: 两重意已上,皆文外之旨,若遇高手如康乐公览而察之,但见性情,不睹文字,盖诣道之极也。(《诗式》卷一) “二重意”说:“曹子建云:高台多悲风,朝日照北林。王维云:秋风正萧索,客散孟尝门。王昌龄云:别意猿鸣外,天寒桂水长。”都是即景言情的例子,情在景中,意见言外,乃殷瑶“佳句辄来,惟论意表”的申发。两重意之说已经暗含了司空图味外味的胚胎。至于“但见性情,不睹文字”,分明是“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的前奏。皎然承王昌龄《诗格》,在诗歌风格分类上也有贡献。他将诗分为十九种类型,为“高、逸、贞、忠、节、志、气、情、思、德、诫、闲、达、悲、怨、意、力、静、远”。每一种类型后面还有一句解说,其中与神韵有关有以下三种:情:缘境不尽日情。静:非如松风不动、林狄耒鸣,乃谓意中之静。远:非如渺渺望水,奋奋看山,乃谓意中之远。皎然对“情”字的解释超出了钟嵘的“文已尽而意有余”,直接将“文”落实为“境”,而境则似应解为兴象的组合。关于静和远,皎然释为景物与心情之间某种默契的联系。王士稹在早期标举“远”字纲领时恐怕受到过这两个字的影响。钱谦益评价说:“截断众流,杼山之微言也。”皎然《诗式》的整个美学倾向与王士模的好尚相近,钱氏所评当无误差。 唐末司空图可说是唐代神韵论系统的集大成者,他也是对清代王士稹影响最大的人物之一。司空图的诗论最典型地体现了唐人论诗感性化的特征,思考的独特性和思考的不周密性都反映在他身上。从形式上看,司空氏的理论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论④j麓妻j童。 有形成定论的情况下,我们依然将此归于司空氏名下。正如不少评论家指出的,司空图诗论的核心是“味外味”说,在《与李生论诗书》中,他有一段著名的论述: 文之难,而诗尤难。古今之喻多矣,愚以为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也。江岭之南,凡是资于适口者,若醋,非不酸也,止于酸而已;若盐,非不成也,止于成而已。中华之入所以充饥而遽辍者,知其成酸之外,醇荚者有所乏耳。彼江岭之人,习之而不辨也,宜哉。……噫!近而不浮,远而不尽,然后可以言韵外之致耳。……足下之诗,时辈固有难色,倘复以全荚为上,即知味外之旨矣。所谓味外味,就是味外之旨。以味言诗,起于南朝时期,“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此项专利权不属于司空图。至于味外之旨,严格地说,也不属于司空图所创。皎然《诗式》早已提出“文外之旨”。司空图的“昧外味”说必须和他的“象外象”理论结合起来,才构成新的贡献。吴调公在《神韵论》一书中指出:“味外之旨是和象外之象密切联系的。”实在是中的之言。不领略象外之象的人就无法懂得司空图的味外之旨。味外之旨比较好理解,主要意思是一句话中包含了两重意义,象外之象理解起来比较困难,司空图诗论的不严密性就体现在这,不能用理解味外之旨的方式去理解象外之象。前面的那个象指的是客观景物本身,后面的那个象指的是诗人情思熔铸过的审美境界。司空图的原意是:山水诗中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实地实景的如实描写,读者可以按诗索地,境与诗合。另一种是亦真亦幻的艺术世界,读者只可以在诗中观赏,却找不到真实的处所, 谈哉!” 戴容州云:“诗家之景,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岂容易可谈哉!然题纪之作,目击可图,体势自别,不可废也。愚近作《虞乡县楼》及《柏梯》二篇,诚非平生所得者。然“官路好禽声,轩车驻晚程”,即虞乡入境可见也。又“南楼山最秀,北路邑偏清”,假会者复生,亦当以著见许。其《柏梯》之作,大抵亦然。浦公试为我一过县城,少留寺阁,足知其不怍也。(《与极浦谈诗书》)从逻辑角度来看,象外之象和景外之景的提法并不科学,而且容易造成误解。但是司空图却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味外之味与诗中的山水境界,有一种内在不可分的关系,那种似真似幻、只可远观、不可近玩的艺术世界总是让人流连不已,体味不尽。原因何在,司空图也讲不清楚,他只能感叹“岂容易可谈哉!”作为一个悟性敏锐的诗评家,指出这点已属不易。 司空图诗论的另一个部分是《二十四诗品》。正如清代刘坛所指出的:“《诗品》之作,耽思旁讯,精骛神游,乃司空氏生平最得力处。”这部著作以诗的境界论诗,理论蕴藏在境界之中,应属于诗化的理论。其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从鉴赏学的角度具体印证了味外之旨。第二,对诗人构造境界的过程作了一些探讨,接触到某些创作心理方面的问题。司空图《诗品》将诗的风格划分为二十四种类型,又称二十四品,每一品都冠以一个名称,然后又用诗的形式对各品中的境界作了描述和解释。这二十四品实际上并 四品,为雄浑、冲淡、沉着、高古、典雅、劲健、自然、豪放、疏野、清奇、悲慨、超诣、飘逸和旷达。另一类属于艺术修养和写作技巧范畴,有七品,为含蓄、精神、缜密、委曲、实境、形容和流动。第i类属于语言风格,有三品,为纤浓、洗练和绮丽。三类中最重要的是总体风格,它们具有统摄的作用,其余诸品都在不同层次和角度上向它们靠拢,为其提供证据和基础。十四种风格其实又可以分为两部分,各以一个统领风格为代表。吴调公在《神韵论》中指出:“应该承认,《诗品》的美学范畴是多样的,具见作者能博采兼收,然而在多种范畴中,基本内容,亦即诗人的美学理想,仍自可见:突出雄浑,冲淡二品。”可谓深得作者之旨。 雄浑与冲淡处在众品之首.代表着两种不同类型的艺术风格,一宏伟壮大,一冲和澄澹,一力度非凡,一微希恬敖,一外露,一内向,几乎具有对立的倾向。雄浑方面有三品归于麾下,为劲健、豪放和悲慨,它们是唐诗中风骨型作品的归纳和概括。至于冲淡一类,阵容庞大,它们才是神韵风格的汇集。作者对冲淡的描述: 素处以默,妙机其微。饮之太和,独鹤与飞。犹之惠风,荏苒在衣。阅音修篁,荚日载归。遇之匪深,即之愈希。脱有形似,握手已违。冲淡一品的核心在静默淡泊,得意忘形。要非情思高远,形神萧敖者,不知其美。归于冲淡麾下者有沉着、高古、典雅、自然。疏野、清奇、超诣、飘逸、旷达九品,足见作者对神韵类风格的重视和偏爱。王士稹曾经说过,二十四品中冲淡、自然和清奇三品为品之最上者 俯拾即是,不取诸邻。俱道适往,著手成春。如逢花开,如瞻岁新,真与不奇,强得易贫。幽人空山,过雨采蓣,薄言情悟,悠悠天钧。 娟娟群松,下有漪流。晴雪满汀,隔溪渔舟。可入如玉,步屑寻幽。载瞻载止,空碧悠悠。神出古异,澹不可收。如月之曙,如气之秋。此三品描绘的都是素淡的景致,满眼看去,尽是白色和绿色。在淡到几乎看不见诗的时候,透出一种奇趣。这就是苏轼所说的“发纤浓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我们也可以说,所谓“遇之匪深,即之愈稀”、“神出古异,澹不可收”,也就是意中之远。每段赞诗都有一至几个自然景物构成的世界,它们彼此之间互相呼应,似断还连,此即人与景物构成的艺术境界。宗白华在《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一文中说过:“化实景而为虚境,创形象以为象征,使人类最高的心灵具体化,肉身化,这就是艺术境界。”这段话恰可移来形容司空图的诗境。艺术境界也就是象外之象,象外之象传达给人们的即是味外之旨,而所谓味外之旨,实际上是指艺术境界中含有的心灵化的东西。 司空图的审美理想是偏向于超越现实的,冲淡一类品格所描绘的都是山林田园隐居的生活,其情趣也是隐逸旷达的类型,这种隐逸和超脱并不带有反观现实的意味,它们缺少对生活本身的体悟。这种现象说明作者在表述神韵派理想的过程中渗入了晚唐时代的特点,“是他处于唐王朝极度衰乱中产生的消极悲观思想在美习.j墨妻÷0上《 的味外味之外,显然也包括这种美学倾向在内。王氏字“贻上”据说也凶司空氏而起,“司空图隐于祯贻溪上,王阮亭名字盖取诸此”(鲍诊《稗勺》)。但是王士稹真正钦慕这种倾向还是在晚年,即所谓太音希声,造平淡之时。自司空图这里开始,“神韵说”的理论中带有了这种特色。 除了十四品的风格外,属于创作方法和语言修辞的其余十品还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作品的表达和风格的构造。这个部分缺乏系统性,涉及的面较泛,但还是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含蓄”一品,言:“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语不涉己,若不堪忧。是有真宰,与之沉浮。”此品提出了一个创作原则,要求诗人将主观情感完全纳入景物描写之中,做到一句话、一个字的正面表达都没有,而读者观之,却已尽得风流。这等于把味外之旨推到了极端。王士稹在《香祖笔记》中说:“表圣论诗,有二十四品,予最喜‘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八字”。其实此八字是由皎然“但见性情,不睹文字”引申而来。后来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提出“羚羊挂角,无迹可求”也是此一原则的继承,“不著一字”遂成为神韵系统一条公认的原则。 关于艺术境界的构造过程,司空图也做了一些探讨。他在《缜密》中指出“是有真迹,如不可知,意象欲出,造化已奇”;在《精神》中指出“离形得似”;等等,特别是在《实境》中提出的“忽逢幽人,如见道心”一句,对于人与景物交流的偶然性与必然性,理性与直觉,有限与无限,瞬间与永恒等问题,有所感悟,有所表达,可谓难能可贵。但是,总的来说缺乏系统性,表述也不够明确。或许这是以诗论诗的一种局限。 仍不失为神韵诗学发展史上的一块里程碑。 宋代诗歌的主流与神韵理论是背道而驰的。尚议论、尚学问、尚思辨和讲理趣是宋诗的主导倾向,尽管还有一些趋向不同的流派。但并不占重要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宋代诗论的兴趣多不在神韵方面,即使有一些,如王士稹曾提到过的姜夔的《白石道人诗说》(见《渔洋诗话》),其深度也远不如唐代,这种状况直到南宋后期严羽《沧浪诗话》问世为止。严羽的诗论在宋代不属于主流派,而是作为主流派对立面出现的。严著《沧浪诗话》目的是为了批评主流派,并企图扭转诗坛的风气。在这一点上正好与司空图相反。正因为怀有这样的出发点,严氏的诗论针对性特别强,全书的重点就在于对宋诗弊病的探讨和诊治,这使得他的诗论显得不够全面。但其针对性也带来了严氏论诗的独特性,他本人曾经自诩说: 仆之《诗辨》,乃断千百年公案,诚惊世绝俗之谈,至当归一之论。其间说江西诗病,真取心肝刽子手。(《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严羽把他的手术刀对准了江西诗派,自以为抓住了主流派的病根,可断千百年之公案。他在《诗辨》中这样概括江西派的病根: 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益于一唱三叹之音,有所歉焉。且其作多务使事,不问兴致,用字必有来历,押韵必有出处,读之反复终篇,不知著到何在。一@垂,素÷塞忠 趣。它们是宋代诗坛的风尚,也一度是宋诗的特长所在。其实议论为诗在晋代就出现了,那时叫“玄言诗”。再往下,陶渊明、谢灵运诗中都有议论。至唐代,杜甫首开议论,影响深远。中唐韩愈又启文字、才学为诗的风气,实为宋诗的先驱。宋人引进散文笔法,以生新代替软熟,以议论助其酣畅,力避旧途,凿拓新径,在诗歌史上自有其不可抹杀的重要地位。问题在于江西派末流将上述因素推到极端,挤掉了诗之为诗的安身立命之所,于是就出现了一种诗的迷失:“读之反复终篇,不知著到何在。”严羽的批评是击中要害的。其实指出这一点的人南宋初就有了,张戒在《岁寒堂诗话》(卷上)中说:“子瞻以议论作诗,鲁直又专以补缀奇字,学者未得其所长,而先得其所短,诗人之意扫地矣。”南宋末刘克庄又指出:“游默斋序张晋彦诗云:近以来学江西诗,不善其学,往往音节聱牙,意象迫切,且议论太多,失古诗吟咏性情之本意。”(《后村诗话》后集卷二)两人的批评可以说都切中了宋诗的弊病。然而诗之为诗,“本意”究竟何在,他们未作深究,仅论到吟咏性情为止。严羽的贡献就在于,他作了进一步的探寻和挖掘,并在创作论域找到了新的结论: 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且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而其诗独出退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惟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 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以禅喻诗在宋代是一种风气,但人们谈论的都是怎样学习做诗,把琢磨前人的经验当作参禅来对待。严羽自己也受到这种风气的影 的妙悟却是另外一个意思,它是指一种创作心态。妙悟一词本从佛家来,《涅檠·无名论》说:“玄道在于妙悟,妙悟在于即真。”意思是说,对佛理的认识在于学者自我领会,既不依傍外人,也不依靠理论的推衍,要靠直觉去把握本质和根源。禅宗六祖惠能还说过这样的话:“善知识,我于忍和尚处,一闻言下便悟,顿见真如本性。是以将此法流行,令学道者顿悟菩提,各自观心,自见本性。”(《法宝坛经》)惠能对于禅悟讲究一个“顿”字,强调突然的、瞬间的领会,摆脱繁琐的理论,超越逐级的渐进,一瞬间抓住本质,光明透顶,一通而百通。严羽所言诗的当行、本色,就是指这种类似于禅道的创作心态。过去人们的批评,往往集中在诗歌的内容上,即吟咏情性还是阐发哲理,或者堆砌学问,严羽却发现诗之为诗,其本质不在诗歌的内容,而在于创作的心态。韩愈的《陆浑火山》通篇写的都是自然景物,然而排比铺陈,争奇斗险,没有妙悟,所以缺乏一唱三叹之音,缺少诗味。这种情况宋诗中有不少。相反孟浩然做诗,讲究“伫兴而就”,一味妙悟,因此他的诗“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关键在于妙悟。妙悟对严羽来说,就是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严羽找到了诗歌的本质,也就找到了江西诗派的病根,从今天的角度来看,他把中国古代对于诗歌的认识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如上所言,严羽论诗关注作家创作的心理过程,对于创作的对象,并没有作专门的论述,这是一个弱点。佛家的妙悟旨在佛理,这是很明确的,那么诗家的妙悟又在何处呢?根据上面所引的严羽原话,可以推断出,作者指的妙悟肯定包括孟浩然一类的自然山水、田园风光的题材。有人因此认为严羽就是片面地崇尚王、孟冲淡闲远一路。“故止能摹王孟之余响,不能追李杜之巨观也。”(《四库全④i曲妻.童。 “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离别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又在《诗辨》中说:“诗之极致有一,日入神。诗而入神,至矣,尽矣,蔑以加矣!惟李、杜得之。他人得之盖寡也。”这些话当然不是故作恭维。另外,严羽又说过:“工夫须从上做下,不可以下做上。先须熟读楚辞,朝夕讽咏以为之本,及读古诗十九首,乐府四篇,李陵、苏武、汉魏五言皆须熟读,即以李、杜二集枕藉观之,如今人之治经,然后博取盛唐名家,酝酿胸中,久之自然悟人。”这里说的悟是否也包括在妙悟当中呢?作者并没有说明。除此之外还有“汉魏尚矣,不假悟也”,该作如何理解,也没有诠释,这些都影响了对妙悟的把握。 作为一位真正的外科大夫,既要挖出病根,也要开ffj良方,指出一条疗治的道路。既然不涉理路,不落言筌,那么作家怎样才能获得妙悟呢?为了解答这个问题,严羽把眼光转向了唐诗,在研究唐诗的过程中他找到了进入妙悟的途径,那就是“兴趣”: 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严氏的兴趣就是别趣,也即别材,是妙悟的入门,所以称为妙悟之门。从这段话看,严羽的兴趣跟殷蹯《河岳英灵集》中的兴象颇为相似,都是指诗人受到自然景物触动而获得诗兴。所谓“透彻玲珑,不可凑泊”,所谓“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正是诗中兴象的特征,也即戴叔伦说的“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炳,可望而不i=.J奢:.?、”、.,t说区别,兴象侧重在作品中的自然意象,而兴趣则重在作家灵感的仰J触发。“兴趣说”作为对“妙悟说”的进一步阐释,一定程度上已接触:并;到了诗歌创作的对象。有人因此批评说:“所谓兴趣,大抵流连光’÷景,风云月露之辞耳,何足贵乎!”“名为学盛唐,准李、杜,实则偏嗜I.王、孟冲淡、空灵一派。”其实未免草率了一点,兴趣只是妙悟的人门而已,是一种触发,不能因此以偏概全。严羽以为诗之风格大体可分为两类:“日优游不迫,日沉着痛快”。“沉着痛快”略相当于司空图的“雄浑”,“优游不迫”则相当于司空氏的“冲淡”,二者都可以从兴趣导人。诗的最高境界即为“入神”,优游不迫,或者沉着痛快都可以入神,惟李杜得之,可见李杜也是由兴趣一妙悟一入神的。对于盛唐,严氏本来并无偏颇,他推出“优游不迫”、“沉着痛快”二品,都是当行,都是本色,可以说无可指摘。但是,鉴于疗救江西诗派之病,鉴于补偏救弊,严羽在贯彻“妙悟说”的时候实际上是更多地借重了山水自然一派,这也是比较明显的。他标举孟浩然而贬抑韩愈,可作第一个例证;以谢灵运直贯盛唐,称透彻之悟,这是第二个例证;“汉魏尚矣,不假悟也”,此是第三个例证。汉魏之所以不假悟,原因在山水自然之作尚未兴起,如此而已。这三个例证可以证明,严羽标举妙悟、兴趣,有依重神韵的用意。严氏对唐代诗学的总结和概括从某种程度上说,也就是对神韵理论的开拓和深化,所以后来王士稹称对严氏兴趣之说“别有会心”,又说:“严沧浪论诗,特拈‘妙悟’二字,及所云‘不涉理路,不落言筌’,又‘镜中之象,水中之月’,‘羚羊挂角,无迹可寻’云云,皆发前人未发之秘。”(《带经堂诗话》卷二)将其奉为圭臬,推崇备至。如果说司空图对神韵论的贡献多在鉴赏论方面,那么严羽对神韵论的贡献就偏重在创作 严羽作为疗救诗病的专家,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诗歌的自身规律上,他提出了透彻之悟。什么是透彻之悟,其实他本人并不知道。离开了人生,离开了对生活的反思,透彻之悟只能成为空架子。严羽大力倡导向古人学习,创造了第一义之说。“学者须从最上乘,具正法眼,悟第一义”,“以汉、魏、晋、盛唐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这种划分疆域、规定程序的学古法有偏重形式的倾向,对明代古典主义产生了深刻影响,甚至盖过了他对诗歌创作规律的精湛总结。在《诗评》中他还公然说过:“诗之是非不必争,试以己诗置之古人诗中,与识者观之而不能辨,则真古人矣。”这使入怀疑,诗人创作的目的是不是以做古人为极则。在这方面,严羽自己患了不可救药的尚古病。在诗歌领域,严羽是后三代复古思潮的源头,他的思想在明清两代分别被古典主义两个时期所借重,是值得人们深思的。 元代是复古意识抬头的时期,正统文学进入了黄昏期。受到金代元好问和南宋严羽的影响,元代的诗歌有一种越过宋诗向唐诗回归的倾向。总的来说,元代的复古还没有形成明确的理论体系,社会意义、文学价值都不高,大部分诗学著作集中在诗格、诗法一类具体写作技法的探讨上,“论多庸肤,例尤猥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这种重视外在形式的复古风气对明代产生了影响。明代的复古风气承元而达到大盛。前期有闽中十子一派,力主唐音。其中高榛编著的《唐诗品汇》将唐诗分为初、盛、中,晚四期,“以为学唐诗者之门径”,在总结唐诗方面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到宪宗成化时期,李东阳创茶陵诗派,以台阁大臣的身份进一步倡导宗唐,开始转变二杨台阁体的风气。李东阳的复古重在音节韵律,主张“诗必 字法,推敲细故末节。所有这些都是南宋严羽以来,在诗歌形式上讲求复古的发展。为文学而文学,就诗论诗是元明两代复古风气的出发点。人们完全不了解文学与时代生活之间的不可分的关系,不了解功夫在诗外的辩证道理,因此,元代的复古学唐,成就反不如宋代,明代也基本如此。这种情况到了弘治年间才有所改观。李梦阳、何景明七子派掀起了一场规模浩大的诗歌运动,将古典主义正式树立为一面旗帜,他们将复古与时代需要结合了起来,把复兴古代诗学作为反对台阁体、革新社会、振奋人心的一种方式、一种途径,如此,古典主义才真正进入了历史。但是七子派的复古,其手段还是停留在体制、格调上,停留在形式的模仿上,因此实际的文学成就与其造成的影响仍然不成比例。直到清初,古典主义诗学才正式步入坦途。 明代古典主义的重点在关心国家社稷,弘扬的是传统的儒家文学观,在风格上也偏向于雄浑悲壮、豪迈刚健,七子派称此为盛唐气象。古典诗歌中明代另有一支重视个人性情的流脉,前人有所忽略,这个非主流诗学的第一个代表就是徐祯卿。徐是前七子的成员,在京城追随李梦阳的学说,但他也曾是吴中四才子之一,怀有另外的美学倾向,他著的《谈艺录》强调以情为本,崇尚灵感,别有一番趣味。引录两段以示: 情者,心之精也。情无定位,触感而兴,既动于中,必形于声。故喜则为笑哑,忧则为吁戏,怒则为叱咤。然引而成音,气实为佐;引音成词,文实与功。盖因情以发气,因气以成声,因声而绘词,因词而定韵,此诗之源也。卉停晰,,以采上.i●m工 也,驰轶步骤,气之达也;简练揣摩,思之约也;颉颃垒贯,韵之齐也;混沌贞粹,质之检也;明隽清圆,词之藻也。高才闲拟,濡笔求工,发旨立意,虽旁出多门,未有不由斯户者也。像文中如此生动、富有才气地描绘情思发生的过程,强调情在创作中的统摄作用,在七子当中是绝少见的。徐氏并非不讲法规,在这方面他反而讲得笼统,讲得宽泛,没有李梦阳等人那么尺尺寸寸。他甚至认为平庸之人才学格调,天才作家须靠冥会,“夫哲匠鸿才,固由内颖,中人承学,必自迹求。大抵诗之妙轨,情者重渊,奥不可测,辞如繁露,贯而不杂,气如良驷,驰而不轶,由是而求,可以冥会矣”,带有一种神秘主义的倾向。后来王士稹论学做诗时说:“越处女与勾践论剑术曰:妾非受于人也,而忽自有之。司马相如答盛览论赋日:赋家之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诗家妙谛,无过此数语。”(《香祖笔记》卷七)恐怕就是受徐的影响。这是一种既不同于格式、声凋,也不同于严羽枕藉古人,久之自悟的方法,看上去更为玄妙。徐祯卿的天才情源论是以自己的创作经验作基础的,也受到了历史上感会、神思一类理论的影响。王士稹对《谈艺录》欣赏备至,在《论诗绝句》中说:“更怜谈艺是吾师”,又说:“余于古人论诗,最喜钟嵘《诗品》,严羽《诗话》,徐祯卿《谈艺录》”,将之与钟嵘、严羽并提。王士稹之欣赏昌谷,一是因为启发了自己突破“格调说”、“悟入说”的重围,指出一条学诗的新路,另一是用情感诠释灵感,突出了抒情诗的本质。徐、王二人都是少年成名,天才颖悟式的作家,彼此有不少相同的地方。可惜昌谷当时为潮流所裹挟,未走上神韵的道路。’…·∥集团中人物,后与李攀龙发生矛盾,被排挤出七子集团。著有《诗家i直说》,也即《四溟诗话》。王士稹曾经认为谢氏诗说“多学究气,愚l矗j所不喜”(《师友诗传续录》),不满谢榛论诗拘泥于字法、句法,又好氍÷改动前人诗句,染有当时的格调风气。但是谢氏诗论中尚有值得称i道的一面。他看到李攀龙等人过于强调模拟,拘于形式,弊端明显,遂将注意力逐渐转向情景关系的研究,在这方面有所探索,有所贡献。试引其两则以示: 作诗本乎情景,孤不自成,两不相背。凡登高致思,则神交古人,穷乎遐迩,系乎忧乐,此相因偶然,著形于绝迹,振响于无声也。夫情景有异同。模写有难易,诗有二要,莫切于斯者。观则同于外,感异于内,当自用其力,使内外如一,出入此心雨无阊也。景乃诗之媒,情乃诗之胚,合而为诗,以数言而统万形,元气浑成,其浩无涯矣。 夫情景相继而成诗,此作家之常也。或有时不拘形胜,面西言东,但假山川I以发豪兴尔。譬若倚太行而咏峨嵋,见衡漳而赋沧海,即近以彻远,犹夫兵法之出奇也。情和景的关系,也就是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自南朝钟嵘、刘勰起就受到诗论家的注意,唐末司空图提出了“长于思与境偕”之说,宋代姜自石也有“意中有景,景中有意”之说(《白石道人诗说》),元代杨载还有“诗不可凿空强作,待境而生自工”(《诗法家数》)之语。明代对这个问题论述较多的是谢榛,谢的观点是强调二者的相因相成,互不可分。“孤不自成,两不相背”。二者之中,又以情为主,所谓 生成,所谓“元气浑成,其浩无涯”。这番论述还是具有相当深刻性的,对此项研究有所开拓。此外他关于触物联类的观点也颇具特色,谢主张作诗不必逼真,贵在随兴而发。就方位言,可以面西言东,就准确性言,“妙在含糊,方见作手”,所以古来好诗“有可解,不可解,不必解,若水月镜花,勿泥其迹可也”。他这番意见是对严羽镜中花、水中月的申发,强调了诗歌创作的随机性、虚幻性,对王渔洋兴发神到之说有明显的启发作用。 王士稹之前,对情景关系作最有价值之论述者要数王夫之。王夫之是继谢榛之后,给予这一问题以最大关注的诗歌评论家。有意思的是王作为明清鼎革之际的重要思想家,其诗学观点却与顾炎武、黄宗羲、钱谦益等人有所不同,他论诗的兴趣,更多地投放在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方面,对这一问题的强调超过了历史上任何批评家,他宣称:“不能作景语,又何能作情语耶?”(《姜斋诗话》)这种意见出现在明清之际,的确发人深省,体现了作者独特的批评眼光。王船山论此对关系,最突出的意见在情景交融。试看其语: 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离。神于诗者,妙合无垠。巧者则有情中景,景中情。 兴在有意无意之间,比亦不容雕刻。关情者景,自与情相为珀芥也。情景虽有在心在物之分,而景生情,情生景,哀乐之触,荣悴之迎,互藏其宅。 “池塘生春草”,“胡蝶飞南园”,“明月照积雪”,皆心中目中与相融浃,一出语时,即得珠圆玉润,要亦各视其所怀来,而与景相迎者也。(《姜斋诗话》) 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溶成一片。这些意思,前人心中其实已有,诗中更是多见,只是由船山明确说出,而且讲得十分明白,自然,一点也不玄妙,依然要算是他的贡献。船山论诗不好创立新概念,不愿自立宗派,这固然使得其理论平易近人,易于被读者所接受,另一方面也使他的观点不够集中,凝聚力不强。比如他论作家的灵感,称:“以神理相取,在远近之间,才着手便煞,一放手又飘忽去,如‘物在人亡无见期’,捉煞了也。”这个思想,实际上也就是王士稹兴会神到的意思,但由于缺少一个理论核心,所以不能与前面的情景诸关系合成为一个整体,很难引起人们的普遍重视。 说到标举理论概念,有一个重要情况值得注意,这就是“神韵”一词恰是在明后期引入诗歌领域的,王船山的《古诗评选》中已见使用,如下数例:神韵所不待论。(评汉高帝《大风歌》)凄清之在神韵者。(评谢跳《同谢咨议咏铜雀台》)一泓万顷,神韵奔赴。(评贝琼《秋怀》)王船山的神韵,并不是作为自己的理论中心来使用,且未与诗话中的情景理论结合起来,所以不能算一种创见。从所引评语来看,船山的神韵略相当于“生气”一词,很显然王夫之是受到了当时评论界的影响。 嘉靖、万历年间就有人于诗学界标举神韵,最早的是汾州孔天允。王士稹论述神韵时引用过孔氏的一段话。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到孑L天允倡言神韵曾受到薛蕙的启发,薛蕙身处前七子勃兴之时,对 谢灵运、王维、孟浩然一派,标举清远,孑L天允遂认为“总其妙在神韵矣”。孔天允在嘉靖、万历年问并无声望,创作成就平平,朱彝尊《静志居诗话》称其“如新调鹦鹉,虽复多言,舌音终强”。所以他的观点没有受到注意。稍后于孑L文谷,更多地使用神韵一词以评诗的是兰溪胡应麟。刊刻于万历十八年的《诗薮》是一部颇具影响的著作,胡氏在此书中论历代各体诗歌,使用“神韵”二字达二十余次之多,可见已非偶然为之。其中有一些地方,用法接近于王十稹,如: 二谢题戏马台,则并题面不拈,但写所见之景。故古人之作,往往神韵超然,绝去斧凿。(内编卷五) 若神韵干云,绝无烟火,深衷隐厚,妙协箫韶,李颀、王昌龄,故是千秋绝调。(内编卷六) “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神韵无伦。(内编卷六)应该说,这些地方王士稹承继了胡氏。其实胡应麟论历代诗,尤其是论唐诗,不少地方与王士稹相似,如称陈子昂、张九龄并开盛唐之风,陈开古雅之源,张创清淡之派。王士稹在《唐贤三昧集序》中也说:“张曲江开盛唐之始,韦苏州殿盛唐之终”,明显受到了胡氏的影响,但未见称引。胡氏使用神韵,也有与王士稹不同的,如:“初唐七言律褥靡,多谓应制使然,非也,时为之耳。此后若《早朝》及王、岑、杜诸作,往往言宫掖事,而气象神韵,迥自不同。”(内编卷五)总的说来,胡氏运用这一概念,含义是宽泛的,大致上指诗歌体现出来的内在精神面貌,他自己就曾明确解释过该词的意义: 也。筋骨立于中,肌肉荣于外,色泽神韵克溢其间,而后诗之荚善备。(外编卷五) 这种诠释可以说代表了明代大多数关于神韵的评论,包括后来的陆时雍,他的《诗镜》也以神韵为标范,所谓“拂拂如风,洋洋如水,一往神韵,行乎其间”,意思上略同于王船山。还有胡震亨的《唐音癸签》。全袭胡应麟之说。所有这些,代表了诗学界一种新的动向,预示着古典主义诗论的新的变革。王士稹于清初标举“神韵说”,掀起新的创作潮流,正是以明代后期的酝酿和准备为依托的。这样,明代实际上成为神韵诗学传统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 “神韵”一词由来已久,源远流长。它最早是作为人物评论来使用的,见载于南朝的史籍。如“神韵冲简”(《宋书·王敬弘传》),“神韵峻举”(梁武帝《赠萧子显诏》),专指人的精神气质。六朝时期注重人的内在精神品质、标榜个性,此类词汇遂颇流行,诸如“风韵”、“思韵”、“高韵”、“远韵”、“风神”、“风气韵度”等,大体上意思相同,而又各有侧重。以后引入画界,借作人物画的品评,成为一个艺术概念。谢赫《古画品录》有“神韵气力,不逮前贤”之语,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又有“人物有生气之可状,须神韵而后全”。自此神韵演变成了艺术作品的一种属性,脱离开对人物的直接评价。但是其内涵依然是作品中表现出来的人的精神品质,一种无形的、存在于笔墨之外的东西。明代诗评界正是从画界将其移人诗歌领域的,当时的目的恐怕主要是矫正七子派学古徒具形似的毛病,所以保持了它原来的内涵。到王士稹才在原有内涵的基础上赋予了弋,舅孕;÷0。,∥卜、l |
Publisher | 山东人民出版社 |
Date | 2018-03-05 2009-03-31T16:00:00.000Z 2021-10-29 |
Type | 旧方志条目 |
Identifier | https://fz.wanfangdata.com.cn/details/newItems.do?Id=11269342 11269342 978-7-209-04767-8 |
Language | zh |
Source | |
Coverage | K828 |